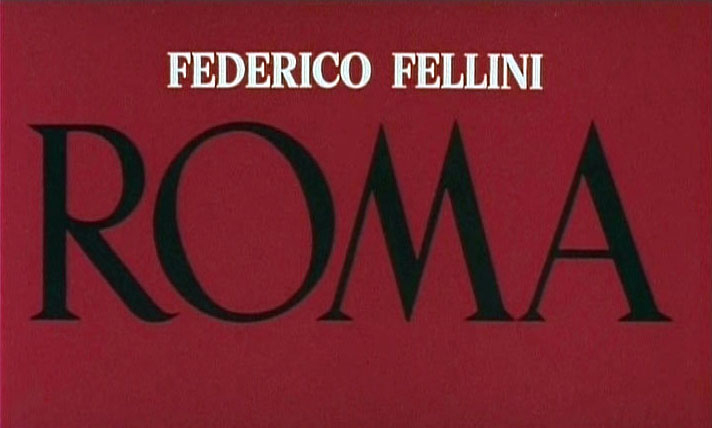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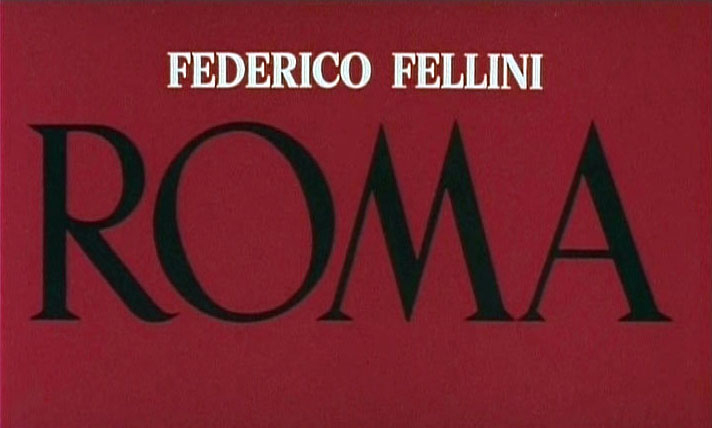
罗 马
——费利尼
|
“罗马是什么?”我最多只能试着说说我听到“罗马”这个字时联想到什么。我也常常这么问自己,所以大概还能说说看。我想到一张像索迪、法毕利兹、码尼亚妮的粉红色的脸:一副因为食与性的需要而忧心忡忡及沉重的表情。我想到一个褐发、脏兮兮的南方佬,一片开阔、支离破碎的天空,衬有割据舞台般的背景,紫红、荧光、浅黄、黑和银色的,哀伤的颜色。但总的来说是一张教人安心的脸。教人安心,因为罗马允许你做任何一种垂直思考。罗马是一个水平的城市,有水有土,大刺刺横卧,所以是梦幻翱翔的理想起落台。始终在两个不同范畴——事实与幻想——之间矛盾挣扎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这里找到了对他们脑力云做极适度和无制约的助力:有一条脐带把他们结实地与现实连在一块儿的安心。罗马是一位母亲,一位完美的母亲,因为她漠不关心。是一位有太多孩子的母亲,所以没有时间理你,从不向你要什么,也不期待什么。你来的时候她接纳你,你走的时候任你自去,像卡夫卡的法庭。这蕴涵着古老的智慧,几乎是非洲的、史前的。我们知道罗马是一个以历史闻名的城市,她的魅力正在于无牵无挂出现在某些苍茫荒凉景色上的老旧不堪和原始,在于看起来像出土化石、嶙峋有如长毛象残骸的废墟。 如果要说这样的安心有它的负面效果,如果说在罗马很少有精神病患,倒也不假。心理医生认为,得精神病是运气,有助于深入发觉自己,如同跃入大海寻找传说中的宝藏,使小孩不得不变成人。而这一点罗马做不到。她大腹便便和慈爱的外貌可以预防精神病,但也抑止发育和真正的成熟。这里没有精神病患者,但也没有成人。这是一个无精打采、事事怀疑和没有教养的孩童的城市,还有一点残障,心理上的,因为阻碍发育是违反自然的。 也因此,在罗马对家庭有着格外的依恋。我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其他城市听到有这么多亲戚可谈。“这位是我的妹夫。喔,赖罗,他是我表哥的儿子。”是一串锁链,活在限定的和彼此熟识的人之间,是以生物关系建立起来的公社。像一窝小猪、一群刚孵出来的小鸡那样活着...... 不过罗马仍是完美的母亲,不逼你循规蹈矩的母亲。就连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你算老几?你谁都不是!”也教人宽心。因为这不止是轻蔑,也是自由。你谁都不是,所以你可以是任何人。身事都可以做。可以从零开始。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罗马着般被人辱骂过,但她不还击。罗马人说:“罗马又不是我的。”罗马人抹去事实,说“关你屁事”,或许源自于他对教皇或宪兵队或贵族阶层的惧怕。把自己关在一个食与性的圆圈里,于是,他关注的事少之又少。 在某些平民区,为了问“你好吗?”真的是得说:“今天早上大便了吗?”我初到罗马的时候,这样的粗鲁、没有骄阳,老被拿来当笑话讲。例如,店员憎恨地看着你,因为你进来打扰了他们的空虚、懒惰。或者,当你问路的时候,为了思考在类似这样的冬眠期被打扰。 老百姓和贵族阶层有些东西是一样的。比方说,对母亲的崇拜。罗马贵族是农妇、女地主、女教皇。看仔细点,罗马贵妇跟女门房很像。除了炫耀方言以外,老百姓和贵族的谈话内容是一样的。感觉上他们在一个不知道自己是死人的坟场里游荡。跟他们相处让人觉得困窘,不知道谈些什么,他们会问出教人不悦的问题,他们不读书,无知被认为是权利。这些贵族,通常从来没有出门旅行过。他们的兴趣是:马、打猎(有人数羊)和生意。买进、卖出。稍微让他们比较振奋的话题是征收、税制(“你认识布雷提部长吗?他到底要什么?”)。 只要这个时候,黯淡的目光才略显生气。罗马在不希望被打扰而且是最严谨的教堂产物——无知的人手中。热爱家庭的无知的人。这种人完全受到固有的几世纪以来的环境制约,以至于相信他应该只能这样活着。一个可笑的大宝宝因为爸爸一直打他屁股而满心欢喜。 衡量我和罗马人的关系,似乎结论只能是罗马人无法给我任何有用的东西,即便就个人层面而言。把罗马歌阶层的脾性具体化以后,得到的是一个沉重的影像:忧郁、奄奄一息,让人联想悲观、沉滞的幽灵,昏昏欲睡、自弃、反对的眼神,没有好奇心,要不就认星球的城市。这个为好奇心没什么用。也许这是一张极度衰老的脸,把所有一切都消化完毕后如今轮到他被消化,变成排泄物,耗尽他所有的感觉,回归为尘土,为肥料。这奇特的气氛也要归咎于罗马爸爸、罗马妈妈,他们就只知道尿啊尿啊,你小时侯的尿尿之事。说实在的,罗马人小孩从不装腔作势,他说:“你看看多可爱的小脸蛋,可真像屁股。” 飘溢着一锅大杂烩快要烧糊了的氛围:这氛围是教堂所鼓励的,教堂是惟一真正要对这一类长久以来不知天高地厚、不得自拔的意大利人负责的罪魁祸首。然而,这种制约在罗马甚至还得到赞扬。例如,在任何其他城市,一名士兵就是一名士兵。在罗马则否:这里称呼他们为“妈妈的乖儿子”。你看,永远是妈妈的儿子,而妈妈是圣母,或教堂。 我常常自问为什么我拍了一部关于罗马的电影。我的灵感是什么。我是个最不及格的旅行者。偶尔他们提议我拍一些必须要旅行的电影:譬如美国电视台想送我去西藏、印度、巴西,好拍一段精彩的关于宗教及地方魅力的影片。很吸引人的提议,我立刻就说好,但同时我心里有数,我是不会动身的。我最喜欢的路线是罗马——奥斯提亚——维特波尔三角地带。我待在这里很好,所以我的回答是:我拍一部关于罗马的电影吧,因为我生活在罗马,而这个城市我喜欢。但是在这个近因背后还有一个远因。在《甜蜜生活》之后,立刻出了几部以异国之旅为背景的意大利片,如《绿色魔力》等等,一时蔚为流行。那时侯,一方面因为我不苟同,一方面是我真的认为而且坚持不要为了收集奇谈、异闻、惊奇而旅行;身边事物,尤其是身边事物也有其不为人知的一面。其实,正是在自己家里及朋友之间会突如其来地得到某些奇异的启迪、神秘的指引,让你用吃惊的眼睛盯着看。所以从那时侯起,我就开始思索一个旁观者所观察到的罗马,一个近在眼前又远在另一个星球的城市。这个初步构思,几乎不知不觉地随着时间发展为现在这部片子的计划案。 现在这部骗子拍完了,不知道符不符合原先的灵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办法对我拍的片子下评断,以观众的眼光来看它。其实,我根本就不去看它。片子完成时,我就当它已经拍卖掉了:我的工作我做完了,如今轮到它来演给大家看,讨大家欢心。去监视它,我觉得很下流。还有,我想我甚至会认不出它来,在一间大厅里,走了样的环境中,人群、烟雾,还有观众的期待,那已经被他们的听闻和预期心理污染的期待......不,我不去。所以这件评论的工作我没办法做。而且也因为在拍片过程中,片子会脱离你的控制。你拍的不是一部电影,而是许多电影,一次拍一小段。 至于我嘛,有好多剧本里的东西被割舍掉了。我们本想拍一场关于夜游的戏;一场罗马对拉齐奥的足球比赛,一个球迷打赌输了得潜水到英雄广场上的喷泉中......关于罗马的女人;关于罗马的夏季风和云......都留在外面了。最主要被放弃的是维拉诺暮园的戏。在罗马,死亡始终有它亲切、属于亲朋好友的一面。有些罗马人说:“我去看我爸,我去看我叔叔。”结果你发现他们到暮园去了,连这里也有小职员、官僚主义的投影:就算在死人中也可以找到靠山,总会有一名姻亲在天堂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的,这使得死亡不再令人焦虑和神经质。只要想想罗马人叫死者“干瘪教母”。教母,也是有点亲戚关系的。还有,其他一些美丽的表达方式:“他到树梢上面去了”,“他去翻土种花生了”。用这些花生,又回到陈年话题“吃”上头去了。即便在暮园里,罗马仍保有她公寓式的特色,在那里可以穿睡衣散步,趿拉着鞋走路。但这场戏我没有拍。不过在片子里,我相信仍然有墓地辽阔无边、生命熙来攘往,属于罗马的一面。再说,我怎么能全放进去呢?我放弃的东西不计其数。一年有364天你可以完全不与罗马这个城市有瓜葛,视而不见,或者更惨,带着厌恶之死容忍她。但之后,心情恶劣地做在停在红绿灯前面的计程车里,突然间,一条你绝对熟悉的马路,以前所未见的光线和色彩出现在你眼前;有的时候则是一阵轻柔的微风,让你抬起眼睛发现高高的屋檐和阳台耸立在教人喘不过气来的蓝天中。或者是一个声音,一个接近音乐的回声在尘土飞扬、光秃秃的巨大空间内绕着你颤动,你察觉到它神奇地创造了一次刻骨的冲击,一个消除所有紧张的平静感;仿佛在非洲,那儿在你周遭一切的静止与安详不但不会引你进入困倦,反而会让你更清醒和冷静,好像对时间、生命、你自己、生命尽头都有了另一种感受;你从焦虑中解脱,也不再苦闷。 当罗马以她的这种古老魅力笼罩住你以后,所有你对她的负面评价就都消失无综了,你只知道,能住在这里真是莫大的福气。 很遗憾的是在我的片子里并没有这座城市如此米人的一面;我已经拍了太久了,不得不结束掉;再说,我又如何能把这难以言喻的魅力表达出来呢?我曾想到要在片中插入一些看起来出自无心的静止画面,幻灯片式催眠的停格:罗马如画的街景、有大喷泉的小巷弄、被庞然阴影切割的庄严大楼荒芜的景象、悲怆但精彩绝伦的废墟、在白天交错的明亮中或夜晚淫荡的紫红中所撷取的影像;无声、没有意义、神秘的画面;动人心弦的非人之美。 我之前的片子,拍完之后,我便觉得那部片子的主题似乎因为我的工作而枯竭、耗尽、失血。拍完《卡比莉亚之夜》后,考古达到竟然还在那里,没有像剧场舞台布景那样被拆掉,我觉得很荒谬。而在这部电影中,我却有连主题都还没碰触到的奇怪感觉。资料不仅没有耗尽,甚至还原封不动。我一如以往兴致勃勃地做了准备工作,仔细查看城市,到最隐秘的角落去搜寻,但到最后我发现,那些我以为已经掌握住了的地点、人性、大楼、巨大的布景仍未被开发,完整无缺。罗马,依然纯洁无暇,跟我拍的关于她的这部电影一点也不相干。我还想拍另外一部,其他的关于罗马的故事。 |